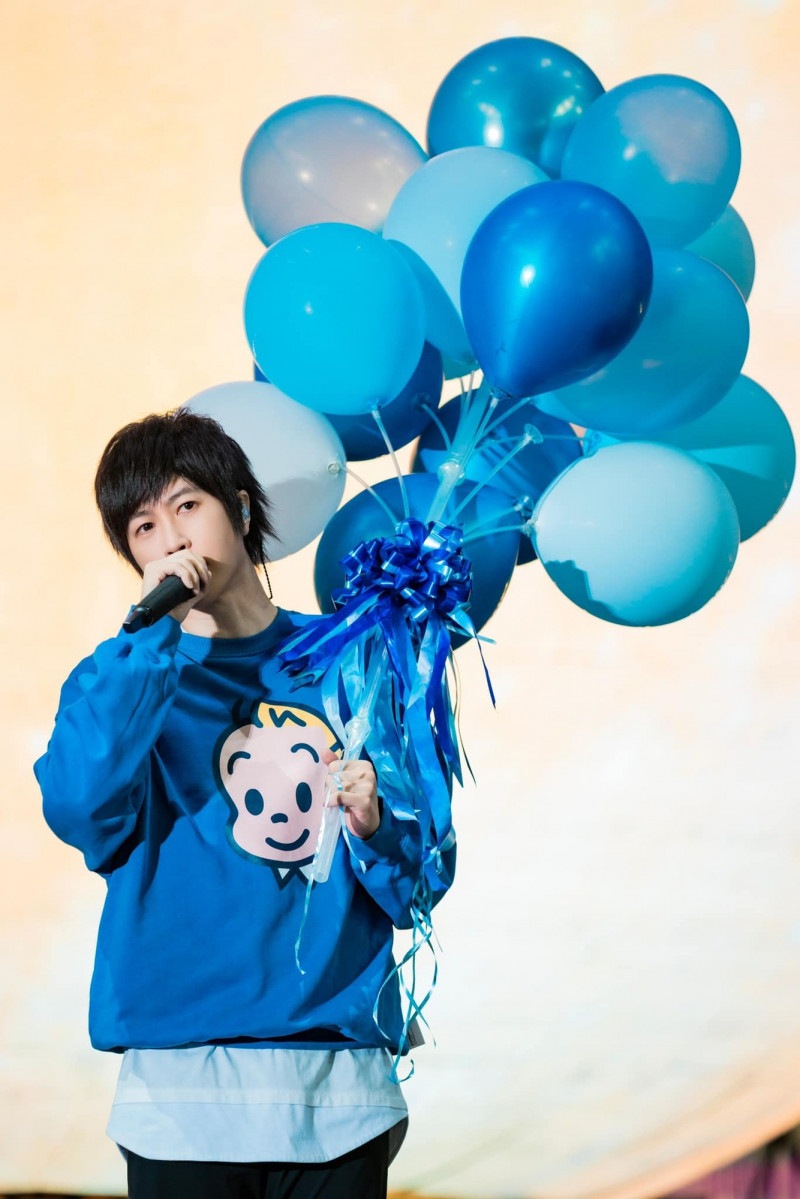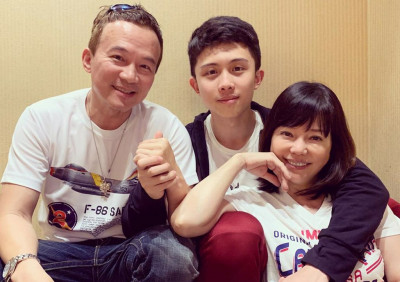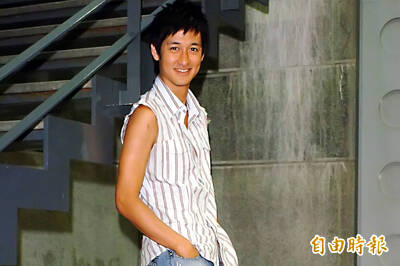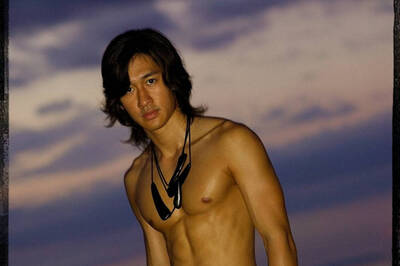李紀/浮雲(在我心中的一個角落飄移著)
〔李紀/自由副刊〕
結束高中教職,正是暑夏季節,我開始在高雄一家報紙的台中分社擔任記者,主跑的是文教新聞。比起以往每天一早就要到學校,新的工作較有彈性,常常是上午十時左右才去市政府新聞聯絡室報到。一些記者會先到那兒交換新聞情報,看看議題,然後就到教育局串門子,看看有什麼事情。
剛開始時,還是有些不慣。比起教書,太動態了。原來跑新聞不只是在一些機關等新聞,還要到有新聞的地方。不過,文教新聞還算靜態,教育方面無非各級學校的人事物,而文化新聞則是當地藝術家、文化人的動態。所幸,被視為省城的台中,區域並不大,市政機構大多在中心區,府會也鄰近,距我住家也幾條街之隔。
每天午後,記者們都會回到報社寫稿,並將各路線記者的稿件一起打包,由工作人員帶到火車站,送上台鐵的固定班次快車,寄送到總社所在地的火車站,交由報社人員領取。截稿後的急件就經由傳真寄送。大約二點到五點時間,辦公室的記者同事,大家振筆疾書。每天大約要寫個二千字到三千字,多篇報導,也包括署名的特稿。
稿子交出寄件後,就鬆了一口氣。記得,因為跑文教新聞的關係,我也認識了一些居住在台中的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藝術家、作家、詩人。有時,也應邀參加聚會,那也擴大了我的見識。本土的、外省的、出身不同、境遇不同,儘管一樣畫畫寫作,但不同的歷史際遇也反映在生活情境。
從中華路轉到公園路,除了夜市還有一些舊書攤,福音教會就在街上,形成某種風景。我常去一處詩人擺設的舊書攤看看有什麼書,也把在其他書攤買到的三○年代中國詩人詩集,拿去給同樣擺書攤的詩人看看。從軍中退伍,以擺書攤謀生的詩人知道我曾在他所屬的《創世紀》發表過詩,很喜歡跟我交談。後來,他知道我曾在《草笠》批評過他們詩社的老大,也不覺得怎麼樣。我常聽他談到從中國被拉入軍隊,糊里糊塗一路跨海來到台灣,從啃饅頭過日子到擺舊書攤營生的滄桑。
因為擔任文教記者,我也報導過擺舊書攤的詩人。看他談到詩那種彷彿生命裡因為有詩而願意活著的一股勁兒,我心裡也有一些敬意。雖然像我這樣讀詩,也寫詩、並嘗試著譯詩的人,也不盡讀得懂他的詩,常常是一些誇張的語句,似乎要燃燒生命,一些突兀概念,說什麼超現實主義,望文生義,後來又成為中國的超現實主義,在西方化與中國化之間擺盪,迷惘中像在追尋什麼,語言中的一些誇張手勢揮舞著。
早春女孩從專科學校畢業了,曾經和我在一張小小單人床,談著談著就那麼睡著了的她,常常在晚上來到我的住處。在自己家經營的鐘錶店幫忙的她,散發一股青春的氣息,比起我常想起的初戀女友梨花,在高中年紀就像冬天,讓人感到某種冷意,她有一股熱情,一股春天的暖意。
有一晚,早春女孩把她裝框的相片放在我書桌,說是要看著我。她來找我時,我正在寫一些東西,想起自己失去的戀情,一種不復返的戀眷。我因這樣的戀眷的糾葛不安而未竟高中學業就離校,想要過浪蕩的一生,先去當兵。但後來又考進大學,修習了歷史。但在一次逆反之旅,並無法挽回自己先說要拋棄的戀情。在島嶼南方,有我遺落和失去的夢。我執意在那夢中,但早春女孩似乎在推開我那個夢。
那一晚,她又留下來陪我。看著她,梨花的影子彷彿過去的春夢又在我眼前出現。我們少小的戀情經歷的肌膚之親,一幕一幕在我心中浮顯。曾經引領我手探觸她身體,又共同經歷了初愛,烙印了愛的痕跡。那些已成追憶的往事似乎纏繞著我,而且又引領我的手纏繞早春女孩。我們相互脫卸了身上的衣服,在時間的過去和現在糾葛的氛圍裡,我端視她裸露的身體上白晢的肌膚,撫摸著她的胸口,並且把自己的頭沉埋在那彷彿山谷的乳溝裡。閉上眼睛的她,只有喘氣的聲音,身體蠕動著,依附我的身軀。我知道早春的女孩不是梨花,我輕聲喚著她的名字,她的名字有雲,彷彿一片雲,飄來與我相敘。
比起初戀時,兩個還是高中生的生澀沉重愛戀,新的戀情輕盈多了,既不須煩惱學業,也沒有其他負擔。就像一片雲,她飄然而至,又飄然而去。她從不過問我曾有的戀情,只滿足於相互廝守時的歡愉。一位開朗的女孩在不怎麼開朗的我的人生裡,彷彿是一些笑聲,清脆悅耳。有時候,她會問我一些採訪新聞的事情,她也會談在家裡鐘錶店的點點滴滴,還透露說她是福州人的家庭,並且以母語調皮地講一些笑話。什麼「福州田太多,厝燒了了。」意思是:「胡椒摻太多,嘴燒了了。」從日治時期以清國僑民定居台中,其實她的家族早已是台中人。
早春女孩讓我從失落的初戀裡重拾新愛。我把梨花藏在內裡的一個角落,在新的戀情裡迎向人生。我不知這一片雲是我人生的過客,或停泊之所,也不想知道,不像初戀時那樣一心一意地寄託。不想讓戀情成為鉛錘繫住自己,不想重複那種難以言喻的痛,只是輕輕地用手細心地托住浮在其上的雲絮,一種無以言說的輕,不在心裡形成負擔的輕。
有一晚,我去拜訪在師專任教的一位畫家。熟悉「五月」、「東方」畫會,也曾師事李仲生的這位畫家,畫畫也寫評,對於時興的抽象藝術有一些見地。我是在一次台中地區畫家的聯展時,在他畫作前端視良久,他走到我身邊跟我寒暄時,約好了去畫室看他。說是畫室,不如說是教師宿舍的一隅,把一個房間當做畫畫的地方,一些美術書冊就在牆角的書架上。這位對藝術思潮具有興味,也頗健談的畫家和我一起欣賞他的作品,談了在台北的美術界,有一種熱情洋溢的夢想。
我向他提到日本小說家芥川龍之介的一篇短文〈泥沼〉,是述及畫展裡,有一位作家在一幅無名畫家的作品前凝視許久。一位記者好奇地問說何以然?這位作家以「傑作」讚歎那幅作品。而這位記者向作家說,畫作的那位無名畫家不久前才自殺身亡的故事。在文學藝術領域,作品的條件和作者的名聲常常不一定成正比,走文學和藝術這條路就必須面對這樣的殘酷現實。
從畫室回到住處,看見屋子裡亮著燈光。春天女孩常飄然而至,應該是她吧。有房間鑰匙的她,可以自由出入,但有時候我未必在。打開房門,我看到側睡在床舖的她,等太久睡著了。我沒有叫醒她,只把房間的燈關了,靜靜地陪在旁邊。但沒一會兒,她就醒了。轉過身來,她的一隻手繞到我的頸項,嘴唇觸及我的嘴唇,熱烈地親吻起來。昏暗的房間只有從窗口照進來月光,一輪正逐漸上升的月亮像一盞燈,從高高的天空照下來。我租居的二樓洋房屋頂層加蓋的木屋彷彿被月光梳洗著,那微光照著春天女孩的肩膀、髮茨,有一種朦朧的美,好像一座森林,而我正走進森林,並迷失在其中。我翻過身來,讓她平躺在床面,輕輕地脫掉她的衣衫,讓月光灑落在她的乳房,並用手撫摸她的臉,從她的耳際而頸項,而胸口,而肚腹,而股間,並且燃起激情的火,兩個人就這樣廝磨著。第二天醒來,陽光從窗外照進來,彷彿聽得見屋外路樹的葉子被微風吹動的聲音,而鳥的吱喳聲也在耳邊交響,還有車聲。
白天跑新聞、夜晚寫作。白天是工作、夜晚是興趣。寫自己想寫的詩,也寫小說以及散文,還有一些文學的評論。我知道自己不一定會在台中停留多久,在這個城市周邊當兵,在這個城市讀大學、教書、擔任新聞記者,算下來八年了。島嶼南方的童年、少年時代記憶仍然深刻印記在腦海。從島國之南恆春半島車城的不到一年小學生涯,到初中在屏東、高中在港都高雄,不到二十歲就離開。但童年、少年時代,島嶼南方海的記憶,田園的記憶、大武山的記憶,往來屏東高雄搭乘火車的記憶、高雄港的記憶、愛河的記憶、壽山的記憶、還有高中時教室磚牆上彈孔的記憶――體育老師小小聲地說的二二八事件槍決學生留下的記號,像生命經歷的形跡,在離開那麼多年,自己從少年變為青年之後,仍然那麼明晰地存在著。
也許有一天,我也會從台中離開,再向北移。為了這樣,我也注意首都的文化動態。在參與《草笠》的編輯事務之外,也思考如果到台北要從事什麼工作。我知道不能靠寫作為生,我也不願意以寫作為生。在我心裡一直記著法國作家A.紀德所說的:「如果有人限制我不能寫什麼,我會自殺。」以及法國詩人保羅.梵樂希:「如果有人強迫我一定要寫什麼,我會自殺。」的名言,我想純粹地寫作,純純粹粹,不為五斗米折腰。可以跑新聞餬口,但不要以文學寫作謀生。這是我的信念。
因參與《草笠》編務,在一期刊物發排了詩人非馬的一首詩〈魚與詩人〉:
躍出水面
掙扎著
而又回到水裡的
魚
對
躍進水裡
掙扎著
卻回不到水面的
詩人
說
你們的現實確實使人
活不了
人間的現實使魚活不了,這是當然的,因為魚活在水中。相反的,詩人活在水面之外的大地。但以使人活不了的魚的說法突顯了詩人的困境,這首詩帶有幽默,讓人在淚眼中微笑。
看稿、發稿、編輯,接觸到許多海內外作品。自己也從中學習了許多。記得,我還以〈愛與孤獨〉寫了一位同輩詩人詩集《孤獨的位置》的讀後感。這位同輩詩人曾經與我在任教的高中共事,另還有一位也修習歷史的同事,在學校曾被合稱三劍客。我以被稱為丹麥文學之父的喬治.勃蘭德斯有關拜倫的評論,以水瓶座這一星象學關心的背景引喻的宿命,延伸的「性愛」(Eros)、「戀愛」(Love)、「同胞愛」(Agape)混合起來而感受的愛的悲傷、苦惱,加以述說。這位同輩詩人離開高中教職後,留學日本,他的《孤獨的位置》留在他的故鄉。
這位同輩詩人的父親,也是一位詩人,從日本語跨越到通行中文,經歷過一段辛苦的再學習過程,他譯介了許多戰後日本現代詩與詩論。我對戰後台灣詩缺少戰後性與時代思想,雖以現代詩為名,卻在精神上流於守舊的古典詩歌情境的醒覺,來自這樣的啟諭。閱讀我參與編輯,並落版的日本詩人田村隆一詩論,以〈地獄的發現、乾燥的眼〉評西脇順三郎與金子光晴;以〈思想的血肉化〉思考鮎川信夫《戰中手記》,不覺眼睛一亮,為那種語言喝采!也感覺台灣詩文學的隱憂。
我發表在《草笠》的一篇有關《文季》創刊的〈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對其中一些評論文章感同身受,對韓國作家全廷漢的小說評介與對文壇忙著讚賞實際上已荒廢的「錦繡河山」的自然詩人舞台的批判有戚戚焉。黃春明〈莎喲娜拉,再見〉、王拓的散文〈廟〉、王禎和的劇本《望你早歸》都出現在創刊號。而有一篇以「史濟民」為筆名發表的〈某一個日午〉,我引述了其中片段,並在結尾說:「讀了這,使我想起了想像中的從未見過的某作家的臉。」那位作家就是陳映真。
春天女孩並不參與我的文學創作,她只是親密地關切我的生活。她會拿我發表的作品閱讀,對我微笑。有時,會陪我外出走走。我們在市街走著走著,在柳川旁邊的一家「純喫茶」喝咖啡。那是專為情侶設置的咖啡館,昏暗的燈光下,高背椅座的私密空間,戀愛中的男女沉溺在情境裡卿卿我我。從純喫茶出來,她往家裡的方向回去,我往住處走,兩人時而回頭揮揮手,走著走著,各自回到自己的地方。
跑新聞和寄情於寫作,工作就這樣交織。漸漸地,曾經失落的戀情被藏在心的角落,現在燃燒的是新的戀情。早春女孩從來不給我心理負擔,她彷彿也知道有一天我也會從台中離開。有時候,她會笑笑地對我說,如果離開台中,不要忘了她。我只尷尬地回應說不會的不會的,我不會忘記妳。她是不同於我初戀女友的開朗女孩,是我的天使,在我感覺孤獨的時際給予我慰藉,而且不求回報。我感到空虛的心被她填補起來。
入秋的時分,舒爽的天氣讓台中感覺更溫熙。跑跑新聞,有時候是展覽,有時候是活動,有時候是體育的運動競賽,像青少年棒球賽,我也專訪一些藝文界人士,常常出現在省府設於台中的新聞處,看到一些文化官僚推動的例行文化工事。省城因中興新村毗鄰幾乎成為相對於首都台北的另一個政治城市而得名,有一些省府機構設置在台中,在那戒嚴的時代,文化只像是妝點社會門面的包裝紙,沒有什麼意義的火花。
氣候在島嶼台灣最為適宜的台中,意外地來了一個中秋節的颱風,早早就在報社發了新聞稿,提前回到住處。為停電也做了一些燭火、手電筒的準備。趁著風勢仍然不強、雨勢也不大的時候,我坐在書桌前,翻閱著由一位德國回來的學者選譯《星火的即興》專輯,譯介為德語的一些台灣詩人作品,包括我的〈景象〉、〈焦土之花〉和〈遺物〉以及〈破滅〉是我的反戰詩,是我1970年代初對戰爭的思考。眼睛停留在詩的行句之間,感覺風雨逐漸變大,呼嘯在窗邊的聲音拍打著樹梢、窗玻璃,而房門響起輕敲的聲音。我起身開門,看見春天女孩流著眼淚,被打濕的衣衫,她靠近我,在我身上哭泣起來。
怎麼了?我急急試著安慰她,一向笑臉盈盈的春天女孩傷心地哭泣著。過了一陣子,她才開口說:家裡要把我嫁給表哥了。抽搐的語氣一再重複這樣的話語,一字一句打在我的心坎。為什麼!為什麼?我追問突然到來的事況。她才說,小時候家裡發生火災,那時候跟舅舅一家人毗鄰,有位表姊為了救懷孕在身的媽媽,及搶救一些東西,不幸遇難。傷心的家人後來商訂了如果媽媽生下女孩,就把她嫁給表哥為妻,做為一種感念、報答。但是,一直沒有讓她知道這門親上加親的婚事。這些時日,家人知道她有交往的對象,認為應該及早讓她知道這件事。不能忘了自己和媽媽的生命受惠於舅舅家的表姊。
就在那個風雨愈來愈大的夜晚,是春天女孩說要與我告別的夜晚,我們要分手的儀式,一種完全釋放感情與肉體的儀式。我有些猶疑,不知道怎樣才好。但春天女孩關了房間的燈,脫掉身上的衣物,也脫掉我的衣服。我們躺在床上對視著,雖然只有窗外的微光,在風雨中仍然沒有停電熄滅的光,但我能看到她肌膚的白皙之色,看到她胸脯的輪廓、身體的曲線,那是我的手親密巡歷過的肉體的土地。風雨聲不歇,我們的交纏也沒有止息。好像世界將走到盡頭,思緒完全從腦海排除,只剩下肉體和肉體的對話。以肢體的語言激烈地相互訴說。通過性愛的門,穿梭在神祕的生命的甬道,像一種旅行,不是以觀照而是以觸撫,兩人相互攀登著暗室的岩壁,潮濕的壁面滴落水珠,而我們必須緊貼著濕滑的路徑,緊緊地手牽手免於被絆倒。
一整夜的風雨遮蔽了月圓的氛圍,一個不是團圓而是別離的中秋夜,我們以肉體的語言相互告白,試著為短暫的戀情留下註記。在我的高中教師生涯和新聞記者生涯之間,一個偶然相識的女孩,她像春天,也像一片雲,停留在我人生,又要飄走了。在訴說分手的儀式,我們互相在肉體上留下離別的記號,像隱匿在肌膚的透明水印,要在特別想念時才會浮顯。這樣祕密會伴隨她的人生,也會陪隨我的人生。是的,就是一種儀式,一種短暫的愛戀印記在心裡的儀式,儀式裡藏著一朵雲,會在春天的晴空中向我拍打回憶的密碼,這浮雲也在我心中的一個角落飄移著。
 圖:吳怡欣。https://www.facebook.com/yihsinwuillustration/
圖:吳怡欣。https://www.facebook.com/yihsinwuillus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