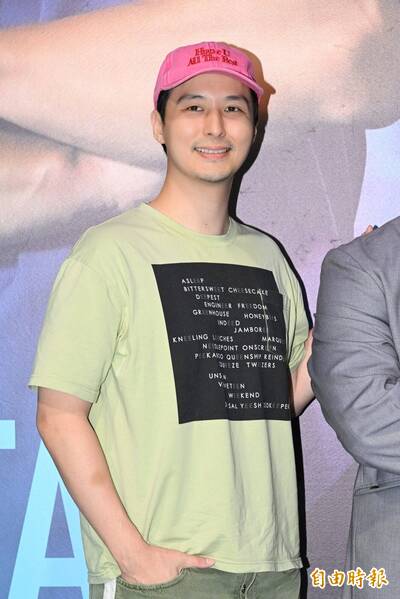陳淑瑤/【閱讀小說】 銀河
〔陳淑瑤/自由副刊〕他們A棟十四樓的公共空間是唯一被管委會評為三A等級的,三戶人家門口連雙拖鞋都沒有,更別說是鞋櫃,臨窗的安全梯道未放置腳踏車或任何雜物,僅幾支收束整齊的長柄傘像任人取用的愛心傘掛在安全門橫桿上。余媽媽將拖把頭高擱在門廳氣窗的窗框上,像匹長征歸來一躍而起的白馬,把桿也不落地。唯一停泊門外的輪椅,余老先生在樓下住了三個月突然與世長辭之後也不見了。自然死亡的蛾類是地面上唯一的物體,來訪的兒子賭物思情,彷彿見到父親魂魄歸來,彎腰拾起那蛾拿去見母親。
夕陽自安全梯旁的窗口照射進來,越過電梯門前,一蓬明光打在門廳瓷磚牆上,屋內人透過貓眼管窺猶覺瞳孔灼亮。天花板上的日光燈暗啞時,對門余家門板上兩張金字春聯若隱若現,好像金爐深處燃燒殆盡的金紙。吉永看見夕陽燦爛,同時收到晚報——一天又消滅了。
那名溫柔體貼在樓下養護所照顧老人的外籍看護,也是在這塊棺材形的長方形門廳接收到情感熄滅的訊息。某日飯後她餵完余老先生八顆葡萄,余媽媽拿出一枚金戒指,感謝她盡心盡力,並做為口頭母女稱呼的定情物,那年輕女孩說樓上宿舍人多複雜,不宜持有貴重物品,請媽媽代她保管。避開所內捉摸不定的耳目,兩人全程使用表情和小手勢。自那時起她便名正言順造訪媽媽家,每次歡喜帶回一個絨毛小娃,令一起工作的室友羨慕不已。余老先生逝世後,她帶著水果來訪,用不見進步的幾個詞彙和余媽媽閒話家常。
某日上午約十點鐘,她在外面按鈴徘徊,喊媽媽斷續喊了不下十分鐘,聲調由怯怯探問變成緊迫哭腔……漸趨平緩哀吟,吉永都看在貓眼裡,那不得其門而入的長髮女孩焦急得拉著門把仰天呼求。連獨善其身的楊媽媽都促她出去看看,擔心出事了。女孩聽見對面門響,立刻低頭向窗邊的樓梯逃逸,留下掛在門把上一袋東西,吉永過去察看,是兩顆沉甸甸像老黃種人乳房的木瓜。
門把上的木爪不見蹤影表示沒事。幾天後兩人在門口相遇,吉永提及此事,余媽媽直言無諱,她沒有體力精神和時間與那女孩在客廳聊天長坐,她在門外按鈴聲聲喚媽媽時她其實是在房底裝睡,「我很能睡!」她強調。又說到那枚金戒指,余媽媽的說法變成是女孩拒收那枚戒指,有點慶幸沒有物證口說無憑,之前約定便不算數了。拒絕回應也是為那窮人家的女孩著想,免得她繼續破費。
女孩又悄悄來過,在門把上綁了隻袋子,袋中的葡萄躺在紙套裡像一串紫色的卵,吉永知道她不會再來了,突然想到松鼠,松鼠不出現,餵食的人將不再施捨,有一股衝動,想扭下一小串葡萄,拿去山上餵松鼠。
盛夏日光充足,她隨手掐熄日光燈,隔壁屋裡的音樂聲愈加泛濫,勁裝的小女生用玩世不恭的怪腔調唱歌,曲調頑皮而歡鬧,幾近撒野。好像音樂太過鮮跳,裡面的人迸了出來;或者,他用貓眼注視外星訪客好一會了。來不及迴避,吉永說嗨,讚歌好聽。
那高個年輕人戴頂帽子,一張蒼白小臉透著新世紀的憂鬱,大概新近姊姊搬走他正快樂自由得無處渲洩,二話不說馬上進屋摘出那片CD,追到電梯門口。她懷疑她聽錯了,他畢恭畢敬一鞠躬說:「請收下這個小東西,謹致歉忱,」說著噘了一下嘴,「不用客氣,這老歌了,好幾年沒聽了!」
她差點笑出來。又是個餵食松鼠的人。松鼠不會挨餓,只是好奇。
出乎意料地母親非常喜歡那片CD,第一次播放時母親幾乎是衝出來的,一踉蹌差點摔倒,她不在家時還會自己去開來聽,聲音之大,不下年輕人。她在門外感受到強烈的節拍衝擊門板,好像裡面開趴,既錯愕又錯亂,沒有馬上開門進去,還聽見她像個孩子似地重複聽著同一首歌。她不知道進門第一句該說什麼,母親卻毫不尷尬。既慵懶又來勁,戲謔淘氣,瘋瘋癲癲,好似未成年的女歌手童妖的喉音喃喃亂吼,母親聽得生氣勃勃臉泛紅暈,好似偷嘗了酒。
「天啊,這種歌說是老歌了!」母親將CD封面和歌書拿在手上研究,絲毫沒有求助於她的意思,自己查字典,「Asteroid」是小行星,「Galaxy」是銀河。這個丹麥合唱團體名叫「The Asteroids Galaxy Tour」。「喔!這叫迷幻搖滾!」她笑著說。
吉永出門時跟她開玩笑:「等一下說不定余媽媽會來打聽這什麼歌!」心底擔憂這樣的興頭上終將過去,她有經驗,隨後會是一大件落寞將人裹住。
她在山路一個大彎道有時可聽見鬧鐘響,「滴滴!滴滴!」不在剛上山,而是走了一段才被喚醒。順著那偵測器般的滴滴聲,她不住地朝腳下的坡地探望,好似那兒有一個城市或一艘沉船被發現了。腳步未有停歇,身體自動順過蜿蜒,有如大型歌劇院看台的坡地,立著形形色色高矮胖瘦的樹木,地上覆蓋植被和落葉。在近處的樹她尚可看見樹幹著地的情形,愈往下俯視就只能隱隱瞥見樹群樹帽,好像全擠在一支漏斗裡了。
滴滴聲漸趨微弱,另一個持續性的機械化的聲音取而代之。一個矮小的女人斜背一只民族風小包,兩眼漠直嘴角下撇邊走兩手邊輪流拍打肚皮,「啪啪!啪啪!」令人想起廣告裡那隻裝了鹼性電池的兔子,不停移動不停打著背在身上的鼓。偶爾其他女人有同樣的動作,為了腸胃健康或者小腹平坦,但這個女人是固定這麼做的,毫無例外,無休無止。吉永拖慢腳步,像廣告裡與活力兔子對照的那隻電力耗弱的疲兔,好讓那積極規律的聲音遠離。
一閃神,背後有個東西鼓槌似地撞了上來,一個不抬起頭的女人連道兩次對不起後超越她,用她聽不懂的語言對耳邊的手機說了些話,驚嚇平復,繼續沿著欄干低頭踽踽前行,靜的時候多,說的時候少,語氣低迷,突然轉頭一彈指把欄干上的餅乾彈落山坡。
她一路沒停地講電話上山,吉永忽然有個念頭閃過,將兩個背影,那個被余媽媽拒於門外的外籍看護和她聯想在一塊,長髮低束,高瘦身材,寬鬆淺上衣貼身黑長褲,拖鞋,在山下的大樓遊蕩也是這一身裝束。
她腰肢柔軟步態輕盈,走上廟口把手機換到左手,對著右側山壁的神像鞠躬,以母語簡短致敬,口氣完全不同,誠誠懇懇,對廟口周邊休憩的人們不屑一顧,繼續上山絮語。
吉永低眉一掃,尋找棋盤上適合稍事停留的棋格,腳步卻不朝它移動,竟是跟隨那個講電話的女人走入另一片樹林,立刻感覺到樹木低矮些,天光耀眼些,最大的差別是道路。以寺廟為中心,接引人們前來的路可說是道路,一氣呵成,此去丘坡凌亂,山路粗糙窄小,沒有整體規畫,一小段一小段地延伸鋪設,逐年修繕,建材和呈現方式皆大異其趣,有像大樓中庭的花圃走道,也有完全素顏的泥巴小徑,最明顯是兩旁不再有一高一低的坡崁。講電話的女人持續駝馳前行,毫不認路,更別說賞景,彷彿抒發心中不快是當務之急,正如美容工作者哲亮說的,必須執行一完整療程始能達到功效。
講電話的女人被電話牽著走,忽而可以看見她的腳行走於耳廓般的梯階,忽而一頭鑽入耳道不見人影。
吉永突然意識到她這一走可是天涯海角地要走回她的家鄉,乃停下腳步目送她離去,她伸手把頭髮撥到耳後,那隻螺旋大耳紅通通的,一旋身消失在岩石後面。不一會一道影子拂過吉永臉龐,頭往後仰看見她踩著一座黑漆鐵架的梯子曲折上升,一隻手持續掩著彷彿受傷血流不止的耳朵,那模樣恍似一支旗子插在高處。
轉身準備離開,意外發現那個女人腳下她剛才擦身而過的坡壁一樹杜鵑正美,紅花一朵朵疊羅漢似地往高處洽光綻放,形成一座紅色花塔,她目不轉睛,想補償錯過了另一株紅色杜鵑的遺憾。那杜鵑長在剛走過的山路,枝幹幾近平傾突出於半空,陰涼峭壁下一年僅此一樹春暖花開。因為它,吉永下了兩個結論,一是紅色杜鵑開得比白色粉色都晚,最晚;二是整個城市就這株杜鵑開得最晚。當然,那是剛搬來第一個春天的事了,母親哼哼笑了兩聲,不予置評。母親不相信是對的,這是個幼稚武斷的想法。即便對她有這麼點意義,後來也來來往往沒擔起頭來,想起時枝頭已添新葉,最後凋零的幾朵花托殘留在樹上,一根根像過了熱水的蝦鬚。有時她是看到路面的落花才猛然想起,今年竟徹底不知不覺。
她又挪了一次碎步以避匆匆行人。放下杜鵑繼續前行。木籬外有零星三五朵兩三朵紅花相隨,定睛一看,又是紅杜鵑,葉片厚圓油亮,根本就是茶花的葉子,幾種知名的花兒她總認得,假面杜鵑這是!哪個多事的女人或男人撿拾杜鵑落花插接在茶樹枝頭,她不是第一次受騙了。
從另一個方向走入廟庭,她忽然亂了陣腳,考慮停留與否,又是找好座位臨時抽身。
又受到不明意圖的驅使,她一路奔回社區,進電梯剛要喘口氣,卻覺得烏煙瘴氣。原以為是山上空氣形成的對比,步出電梯,一股濃煙迎面而來,不需頭腦判讀,鼻子指向右轉,鐵門後門板微開,狂按門鈴卻無人回應。等待的分秒如被人摀住口鼻,她急得彷彿看見門縫飄出煙羽。
警衛組長和一名戴著口罩的銀髮女住戶一路嗅了上來,發現吉永已守在煙窟外稍稍鬆了口氣,兩人輪番按鈴大聲喊話仍無回應,又急了起來。組長貼著鐵門,示意她們安靜,「裡面有聲音,好像老鼠在搬東西……」說著他嗆咳了起來。
居家者和監獄管理一樣,有各式戒規,吉永曉得余媽媽不應門的原因,肯定跟前不久某晚滷肉險些釀禍有關,滷肉據說是她小兒子最愛,一鍋燒成黑炭給冒險衝入的警衛取出扔進樓下垃圾車仍薰臭難聞,居民驚慌搜尋,管理室電鈴響了整晚,總監威脅要啟動消防灑水系統來「洗煙」,余媽媽為了她的家當和絨毛娃娃幾乎要下跪求情,和那次相比,今天小狀況。
吉永大聲叫:「余媽媽!沒人啦!快出來!」
門悠悠地開了,組長氣呼呼揮著煙衝進去,跑到廚房對著天花板上的偵煙探測器邊咳邊罵:「上次說潮濕壞了,修過了還是沒用,禮拜一才剛測試過……」
獨居婦人「張媽媽」責怪余媽媽不該在這時候再噴香水,並使勁傳授許多居家安全須知,組長搖搖頭一聲招呼不打便走了。
余媽媽窗子早就全開了,拿條濕毛巾摀臉,忙著跑陽台換氣並挪來兩支風扇,依然騙不了人。
那張媽媽還是隔壁棟的住戶,末日來臨預備者,今天碰巧打另一扇門進院子,嗅到異味馬上通報警衛展開行動,平安落幕還不肯離開,脫了口罩以煙追物猜了幾種食物,余媽媽都裝傻不答,抓著吉永閒聊,她才怏怏然離開,隔著鐵門又叮嚀:「裡面那扇門沒事就不要關!門口放個幾瓶礦泉水!煮東西記得設鬧鐘……」
「我本來就沒關啊!」余媽媽嘟噥著拿開罩在風扇上頭的塑膠袋。風扇左右擺了兩次頭,索性連扇面上防塵面紗也揭掉了。呆了兩秒,走到門口把吉永拉回來,按下遙控器,絃樂像藤一般細長地自毛絨堆裡抽了出來。她牽著吉永去看藏在陽台洗衣桶裡一小支帶柄鐵鍋,呵呵笑說:「聽音樂聽到睡著!杏鮑菇!我的午餐嗚!」
吉永回到家,輕輕走向母親房間,背靠門框懨懨地看著母親許久。她裹著蠶絲被躺在床邊,突然蠕了一下,說:「說要側睡比較好,向右側,讓心臟在上面,不要壓著……」
「你喔!」吉永拐進浴室撥了一下頭髮,像剛在山上撥弄那借屍還魂的杜鵑一樣,散步向上抹上的一點氣色瞬間灰飛煙滅了,那鍋杏鮑菇倒燒出一張枯皺人臉。
「你這樣不行啦!」她邊走向廚房邊說:「焦味臭成那樣,吵成那樣,你還睡你的!」
「還好啊!什麼焦味?」她一個使勁坐起身來,歎了一口大氣,「哎!天要塌下來,我也頂不住啊!中午吃什麼?」
 photo:michun。www.facebook.com/michun2010?fref=ts
photo:michun。www.facebook.com/michun2010?fref=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