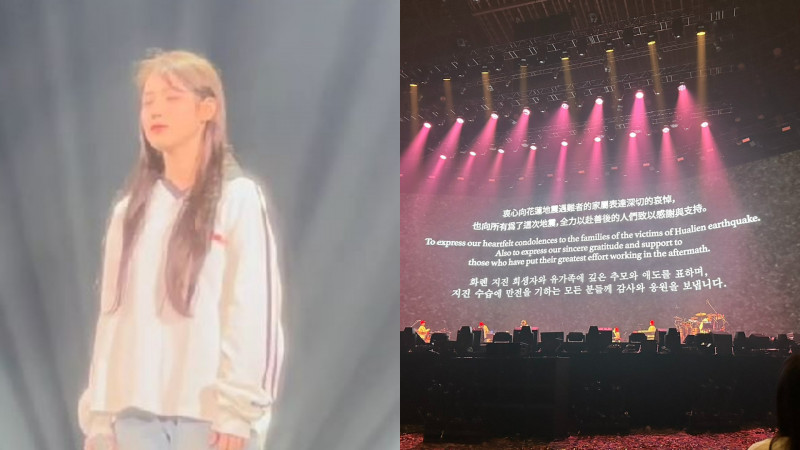香港小說家董啟章最新長篇《愛妻》曝光!
〔董啟章/自由副刊〕小龍的志向,是當一個專業小說家。在決定結婚的時候,我說:你放心寫作吧,不用擔心錢的問題,家裡有我撐住。她卻說:多謝啦!我的目標是經濟獨立。我會有很多讀者!我知道她是個倔強的人,以後也很少在她面前直接談及經濟問題。
做為一個自小在文學培育中成長的人,小龍當然有很高的鑑賞力,但是,在寫作的時候,她不願意被局限於某一類型。她打從心底討厭所謂「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的二分法,但她的寫作並非旨在打破什麼限界。她避免高調和姿態,拒絕任何主義或風潮的標籤,但說她追求的是雅俗共賞,她又嫌太陳俗無聊。她從來不理會什麼社會責任,聽到什麼抗爭、顛覆或賦權之類的呼求,就會頭痛和皺眉,覺得文學不應成為任何立場的政治宣傳;但是,當聽到有人說小說不外乎是「說個好故事」,或者是「說好一個故事」,她又會忿忿不平,好像這樣粗糙的主張把文學的意義貶低。
說小龍想走的是「中間路線」也不對,因為這好像暗示必須對兩方面同時妥協。她只是單純地相信,文學不一定跟大眾無緣,而質和量並不是互相排斥的東西。當然,從實際方面考慮,她知道單靠香港的閱讀人口,根本不可能支撐一個專業作家的生計。所以,她從一開始就把焦點放在她由獲獎而出道的台灣。至於中國大陸,當時的條件似乎還未成熟,但長遠來說也是一個不能排除的對象。她的終極目標,是作品能翻譯成外語,成為一個國際小說家。
對於小龍的雄心壯志,我一直毫無保留地表示支持。不過,對於文學在當今世代的處境,我是個悲觀主義者。我肯定她能夠為香港留下有價值的作品,但要衝出香港,甚至是衝出華語社會,立足世界,並且以寫小說實現經濟獨立,我心裡是不敢看好的。小龍深知我的看法,但我從沒有說任何令她洩氣的話,一直堅決地當她的經濟後盾,讓她無後顧之憂地追求她的理想。然而,也許最後這一點,恰恰說明了她未能達到當初設定的目標。到了她寫作生涯的中期,她也不得不默默地承認,而且陷入了深深的迷惘。
也許,我屬於那些食古不化的高級文學信仰者。像我這樣的人,在創作路上遇到障礙,很容易便會怨天尤人,或者自暴自棄。文壇上也出現過因此而反彈,成為徹底的媚俗者和文學憎惡者的極端例子。我覺得自己依然堅守當初的文學理想。我之所以放棄創作,轉向文學研究,只不過是換了另一種形式,為保存文學價值而努力。如果研究和教學,而非創作,才是我的才能所在,我樂於扮演不同的角色。而能夠同時支持一個富有創作才華的妻子,那真是最完美不過的配搭了。對此,我不但沒有怨言,還感到了深深的幸福。
小龍的第一部作品叫做《圓缺》,是一本中短篇小說集,1998年在台灣出版。當中同題的中篇,就是之前參加台灣小說新人獎的獲獎作品。那是一個關於換心的故事。一個十三歲少年,因為先天性心漏病導致心臟衰竭,急需換心以保命。幸好一個剛去世的同齡女孩的家人,願意捐出女孩的心臟,少年才得以生存下去。少年長大後,查出捐心者有一個孿生的妹妹,便想盡辦法接近對方,甚至跟她一樣報讀了相同的大學學系。男生和女生成為同學和好友,但女生卻不知道男生的身分。男生在女生身上,看見了那個當年救了他一命的女孩的樣貌,有時甚至產生混淆,當她們根本就是同一個人。可是,對方的心明明在自己的胸口裡跳動著。男生發現自己愛上了捐心者的孿生妹妹,對方似乎也對男生有好感,但兩人卻好像被什麼所阻礙而無法發展下去。男生因為一直隱瞞自己的身分,對女生產生歉疚之情。當他發現女生的姊姊當年原來因為給男人侵犯,不堪羞辱自殺而死,而這事件對妹妹造成了不能磨滅的雙重創傷,他的心靈也受到了巨大的打擊,而自己身分的真相也更難啟齒了。他原來裝進了一顆受傷的心,而這顆心同時屬於兩姊妹。男生開始感到自己身上發生某種奇妙的轉變。他的男人身體裡住著一顆女兒心,不但具有字面上的意義,他甚至體會到那位姊姊當年受辱的痛楚,而彷彿同時變成了施害者和受害者。他經歷著身心撕裂的痛苦,在一個突如其來的機會中,忍不住跟孿生妹妹發生關係。這場半推半就的性愛結果以失敗告終。男生痛哭起來,對女生做出了告白,而女生也因為受不住刺激昏倒過去。當讀者以為事情就此終結,男女雙方卻決定畢業後立即結婚,但他們也明白,性在兩人之間是不可能的事情。死去的姊姊永遠也會卡在他們中間,但這也是讓姊姊重生的唯一方法。至於那個曾經侵犯姊姊的人是誰,作者卻沒有交代。
雖然聽起來好像一個頗為濫情的故事,但小龍的寫法卻是非常地克制。無須多說,這篇小說在閱讀時的真正體驗,跟我在上面的複述完全不同。平淡的筆觸、生活化的細節、合乎常情的心理描寫――在看似平平無奇的氣氛中,讀者被一個又一個的揭示殺得措手不及。怪不得其中一位評審有這樣的意見:「在平靜細碎的日常之中,在緩和宜人的節奏之下,上演著一場激烈的內心風暴。作者並沒有譁眾取寵,相反卻是忠實而誠懇地,把處於特殊的臨界點的心理狀態,細膩而生動地描繪出來。」它跟小龍幾篇同時期的少作,合成一個單行本,一出來就大獲好評。這也奠定了龍鈺文小說的基本寫作風格。
兩年後,小龍交出了她的第二本書《平生》。這是她的第一本長篇小說。自此以後,她便以寫同樣的長篇為目標,而完全沒有再寫中短篇了。所謂的長篇,對她而言並不真的非常長,至少不會像比她早出道的D那樣,專寫些令人望而生畏(或者生厭?)的大部頭厚書。小龍的長篇,一般都不超過十五萬字,算是比較輕短。而她的行文,又是比較易讀的,也沒有什麼令人頭暈轉向的形式實驗,所以受到較多讀者的喜愛。她對《平生》能更進一步拓展讀者群,是帶有很大期望的。
《平生》的主角是一位已婚中年女教授,在英國某二線大學教英國文學。她的丈夫是英國人,在同校任教物理學。兩人育有一子一女。女主角在香港土生土長,畢業於港大文學院,背景跟小龍自己有點相似。她後來到倫敦大學念博士,遇到她的未來丈夫,結婚後便在英國定居,沒有再回港。女教授一直過著簡單而安穩的生活,直至有一天,她的班上來了一個女學生。這個女生來自香港,令女教授對她產生親切感。女生十分好學,課後經常留下來問功課,成績也非常優秀,對文學有很敏銳的觸覺。不過,女教授也對女生抱有戒心,總是覺得對方有點古怪。經過整個學期的觀察,女教授放鬆了對女生的戒備,在期考完結之後,還破例邀請女生到她家裡作客,一起慶祝耶誕。這是她教學多年來很少有的做法。女生自此經常到訪,成為了老師女兒的知心密友。兩人終日形影不離,有時女生甚至在教授家裡留宿。後來女兒告訴母親一個祕密――那位女生原來是一個男孩,但卻是個跨性別者,正計畫進行變性手術。女教授對於女生隱瞞身分感到十分憤怒,覺得對方是個不誠實的人,但是在女生的苦苦哀求下,還是忍不住原諒了她。女生於是比之前更融入教授的家庭,連她的兒子和丈夫也對她沒有防範,接受她成為全家的親密好友。丈夫甚至說,女生看起來像是妻子的親生女兒。大家都對自己的寬大和包容有點自我感覺良好。就在大家準備為跨性別女生慶祝生日的當天,女生被問到在生日蛋糕前許了什麼願望,她說:我的願望是,二十五年前把我生下來的母親,能夠認回我這個兒子。女教授當場嚇得昏倒下去。原來她二十多年前隻身離開香港,在英國落地生根,就是為了斬斷一段不堪回首的關係。想不到剪不斷,理還亂。以為已經長埋於地下的祕密,隔了半生還是破土而出。她的心裡浮現一系列的疑問:兒子是為了騙倒母親,才扮演成跨性別者嗎?還是他真的有這樣的性取向?他形成這樣的性取向的原因,跟他被母親拋棄有關嗎?她要為兒子的人生方向負上責任嗎?兒子的出現和親近,是處心積累的計謀嗎?為的是向狠心的母親報復,還是只是渴求尋回失去的母愛?在能夠解答這些問題之前,女教授的家庭,以至於她苦苦重建起來的人生,卻慢慢地開始崩潰了。
《平生》照樣獲得一致的好評,得到了好些獎項,銷量也比《圓缺》增加,但是,距離專業作家的理想還是有一段距離。不過,憑著著作得來的名聲,倒為小龍增添了寫小說以外周邊工作的機會。有一段日子,她經常到中學演講和教寫作班,又在不同的大學擔任寫作導師。這些收入來源並不穩定,而且占去了她不少寫作時間。至於報刊的固定專欄和不定期稿件,稿費相當微薄,除非日以繼夜地筆耕,否則難有經濟上的成果。在這樣的艱難處境下,小龍依然堅持向經濟獨立的目標努力,為的當然不只是一口氣,但也不是什麼女性自主的原則,而是文學應該同時具有精神和物質價值的信念吧。
在種種瑣碎和消磨的奔波之間,她還能在兩年內再寫出新長篇《尺素》,實在是令人驚歎的事情。這次的題材驟眼看來更為大膽。主角兼敘述者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小說家,以大膽的情欲書寫走紅於文壇。有一天她收到一封從出版社轉寄過來的讀者來信,男性寫信人一開始就明言,他是一位在囚人士,正在赤柱監獄服刑。他首先表示對女作家的作品的景仰,感想說得頭頭是道,不像是客套話。他繼而表示自己從小就對寫作感到興趣,但一直苦無學習門路,只是自己胡亂看書和塗鴉,走了不少冤枉路。出來社會工作之後,也曾嘗試在網路上發表小說,不過讀者不多,也沒有什麼迴響。他自知這些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提起來也覺汗顏。自從因魯莽干犯罪行而鎯鐺入獄,回想自己虛擲的前半生,忽然萌生通過文學重獲新生的想法。他細數自己入獄前已經讀過的作者,包括莫言、王安憶、余華、張大春、朱天文等等,都是當代名家。對於香港本地作者,除了女作家之外卻不甚了了,甚為慚愧。他虛心地向她提出兩個請求:一是向他介紹值得細讀的香港作家,二是為他解答寫作上的難題。女作家被這封意想不到的信打動了,覺得此人實在難得,於是便動筆給對方寫了回信。來信人並無詳及他入獄的具體原因,女作家也覺得不便去問。
如此這般,女作家跟這位獄中文學愛好者保持通信。對方的信件時密時疏,但都寫得很長,裡面充滿著求知的熱情,以及自我更新的渴望。因為缺乏正規學習,有時難免會流露出幼稚陳俗的觀點,但也不乏有趣甚至精妙的看法。通信日久,兩人甚至會談及個人生活的點滴,流露出內心深處的感受。囚犯會談及他在破碎家庭成長的痛苦經歷,以及刻骨銘心但卻教人唏噓的戀愛故事,而女作家則忍不住對自己不甚滿意的婚姻作出種種暗示。不過,她始終保持警覺,點到即止。而且,也從不把自己家裡的地址向對方透露。她的戒心令她感到內疚,但對方畢竟是個陌生的犯罪者。
有一天,獄中文友來信說,他下個月將刑滿出獄,重獲自由。他希望能繼續跟女作家保持聯絡。為此,他給她寫了一個某商場單位的地址。女作家收到消息後,如夢初醒。她發現自己心裡冒起了不安,但是又同時按捺不住強烈的好奇。她決定先回信到那個新地址再算。一個月後,她收到從那個地址寄來的回信,信中洋溢著對新生活的熱望。對方表示自己重操故業,當麵包師傅,在一個舊朋友開的西餅店工作。他又透露,正打算以自己的經歷為藍本,創作一部長篇小說。少不免又向女作家請教了一些寫長篇的要訣。女作家對此充滿期盼,對文學的巨大潛移作用也信心大增。就算是一個教育程度不高,來自社會底層,而且又有案底的麵包師傅,也懂得欣賞文學,甚至創作文學。誰說文學只是少數菁英分子的專利?
奇怪的是,女作家回信後,對方卻一直沒有回音。她忍不住親身到那地址查看,發現那真的是一間小規模的西餅店。她遠遠地觀望,又在外面來回走了幾遍,但卻不敢走進去。她竟然害怕被對方認出。為此她感到非常羞恥。如是者連續去了三天,她終於鼓起勇氣走進餅店,裝作選購麵包,偷偷地四處張望。她始終不敢問店員,店裡有沒有一位叫做某某的師傅。回到家裡,她覺得自己的行為很荒謬。就算給她找到他,她打算怎樣?請他坐下來喝杯茶?談論他的小說進度?給他即時的指導和意見?還是給他送上自己的新書?
打消尋找對方的念頭,女作家的生活重回正軌,覺得事情還是告一段落為佳。大概過了三個月,報紙上的一則新聞吸引住她的目光。那是一宗風化案。案中被告某某,被控性侵和意圖強姦兩個年輕女生,因為是剛出獄不久的同類案件的慣犯,被重判入獄十五年。就在同一天下午,女作家收到一包郵件,裡面是一份幾十頁的手稿。一看字跡,就知道是那位獄中文友的手筆。她連忙坐下來細讀,發現是一部自傳式小說的零散片段,前面關於主人翁的成長,中間關於一段純真但最終失敗的戀愛,最後的部分,則是幾次強暴罪行的詳細描述。女作家從未讀過如此驚心動魄而又令人噁心的文字。她感到猶如自己被強暴一樣,極端地憤怒和痛苦,但又同時羞愧得無地自容。與這些粗糙而赤裸的文字相比,自己那些為人激賞的情欲小說,全都顯得異常地虛偽和造作。另外郵件又附上一封短信,內容講述了小說創作的原意和遇到的困難,以及最終放棄的原因。又提到在過往的幾個月,曾經多次在女作家住處樓下徘徊,結果還是緣慳一面。最後他感謝女作家多年來的耐心教導和慷慨分享。女作家像是做了一場惡夢,甚至是生了一場大病似地,好幾個月沒法寫作。家人也不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她決定去監獄探訪那個人。她要代表所有被他侵犯過的女性,去面對他,也彷彿同時是面對自己。不過,她首先得向獄中的他寫信,要求把她列入探監者的名單。最後,她收到他的拒絕信。
 圖:唐壽南。
圖:唐壽南。
《尺素》是那麼尖銳的一個幻滅的故事。我懷疑當中多少反映了小龍的心境。這本書出版之後,評價甚高,但小龍卻好像並不特別感到鼓舞。她漸漸停止寫作以外的教學工作,也不再接受演講的邀請,潛心於下一本小說的創作。這本看似輕盈的小書,叫做《津渡》。故事講一個快將結婚的三十歲女子,一個人去了大嶼山的大澳旅遊。在過河的橫水渡上面,她突然產生一陣天旋地轉的迷失感。她決定在由舊警署改建而成的酒店住下來,沒有通知任何人自己的去向。(其實在寫作的時候,大澳文物酒店尚未建成,而那個靠一條繩子把小木船拖過對岸的橫水渡,卻早已被新建的鐵橋取代。兩者的並置完全是時空跳接。)當晚,在酒店的餐廳,女子遇到一個年約五、六十歲之間的男人。對方問她是否一個人,又問可不可以請她喝一杯。那人說自己在附近開有機農莊,每天早上會親自送食材過來,晚上有時也會過來跟客人聊聊天。他又說自己是大澳人,長大後出去念書,法律學院畢業,在區域法院當了二十多年裁判官,退休後又回到大澳來。女人有點不太相信男人的話,但又對他感到好奇。他既有教養但又有點粗獷的外表也十分吸引。女人告訴男人自己已經有未婚夫,男人立即舉杯祝她新婚愉快。兩人聊了一整晚,男人離開之後,女人回到房間,發現自己對男人的舉手投足沒法忘懷。此後三天,兩人多次會面,男人帶女人四處遊覽大澳,看過棚屋和天后廟,也出過海,上過山。就是這樣的一個定格於不同的風景的、氣氛平靜、結構鬆散、節奏緩慢的小說。《津渡》不像前作般富有戲劇性,情節幾乎沒法覆述。最後,也不知道男人和女人之間有沒有發生什麼,以及會不會發展下去,只知道女主角再搭上那橫水渡的時候,決定取消婚約。
一如所料,《津渡》是個反高潮。它就像一團迷霧,讓讀者看得不知所以然。有評論者認為,在《尺素》的幻滅之後,《津渡》就只剩下風味,而沒有內容或意義了。當然也有人在「沒有故事性」上面做文章,甚至把《津渡》和《去年在馬倫巴》相提並論。那其實也不過是另一種不知所以然,沒話找話說而已。至於有論者反過來認為《津渡》過於通俗,向流行愛情小說靠攏,也就不足為奇了。怎樣也好,正如小說中的女主角正面對人生的轉捩點,《津渡》也可以說是小龍的小說生涯的橫水渡。從此之後,她就沒有再提專業寫作和經濟獨立了。我不是說她放棄創作,而是說,她接受了做為大學教授妻子的自己,不用再去煩惱什麼靠丈夫才能寫下去的閒話,以一個愛好者(也即是amateur這個詞的本義)的方式,繼續她的文學創作。
當然,龍鈺文還是龍鈺文。她不會因為不再著眼於銷量,而轉向冷僻或艱深的方向。對於文學形式的創新和實驗,一向也不是她感興趣的事情。可讀性始終是她的信念。在《津渡》和《朝暮》之間,相隔四年之久,令人一度以為龍鈺文已經「玩完」。這期間她只是出了一本名為《咄咄休休》的專欄文章結集。到了2008年《朝暮》出版,大家終於等到了小說家龍鈺文的回歸。也許由於這樣的心情,讀者對《朝暮》似乎看得比較寬鬆,很容易就收貨了。
做為愛情小說,《朝暮》把「忘年戀」的慣常模式倒轉了――它說的是一個初老女人和一個少年的情感。五十五歲的女主角是一個醫生,在大學保健中心工作,結婚三十年,兩個女兒已經大學畢業。她是個謹小慎微,循規蹈矩,對生活沒有任何不滿的女人。到了這年紀,一心只是等著退休和兩個女兒出嫁。除此以外,前面沒有什麼特別值得期盼。令她完全意料不到的是,一個經常來看病的男碩士生,竟然對她表示好感。男生經常送一些小東西給她,又藉辭約她吃飯。她雖然覺得古怪,但也不以為意,以為只是小男生的戀母情結作祟。曾經在年輕時懷有男胎但卻小產的女醫生,一直對男孩子有著既疼愛又迴避的複雜心理。當她知道男生年少喪母,她便禁不住對他生起憐惜之心。一個學期下來,女醫生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間,對男生產生了微妙的感情,對他的健康和學業,甚至是私人生活也關心起來。當她聽到男生跟女同學交往的舊事,心裡竟然生出了妒忌。她警醒自己不要糊塗,及早結束這段曖昧的交往。可是,男生卻異常地堅決,並且趁機明確地表白,他愛上了比他年長三十年的女醫生。從他半年來的表現,女醫生相信他不是惡作劇,也不是一時衝動,但她沒法接受這樣荒誕的愛。她覺得除了她是女人和他是男人,所有條件也不對。而且,她對她自己的家庭有責任。做為緩兵之計,女醫生說,在男生完成碩士學位前,不要再提這樣的事。如是者又過了一年,男生碩士畢業,他再次向女醫生示愛,並且說:我已經完全準備好了!你呢?女醫生坦白地說:我和你之間,不可能有性。這個我接受不了。男生便說:我不需要性!我只需要愛!
小說的下半部,才是考驗的開始。從向丈夫提出離婚,到女兒的不解和責難,以至於親友的鄙棄,女醫生幾乎失去了前半生累積起來的所有東西。她擁有的就只是獨立的經濟能力和一間自己的房子。她在人世間幾乎尊嚴盡毀,就算是新認識的人,她也不敢向對方披露自己和男生的關係。在陌生人面前,她樂於被誤會為母子而不加解釋。可是,男生卻堅持雙方應該光明正大。為此兩人不時出現爭吵,但是很快又會和解。女醫生決定在退休之前,支持男生完成他的博士學位。除此,她沒有更長遠的打算,也做好了對方有一天要離開她的心理準備。男生卻向女醫生做出承諾,將來成為大學教授之後,要照料她的餘生。最後,男生向女醫生求婚。他們在沙田婚姻註冊處簽了字,兩人勾著臂,靜靜地沿著城門河畔前行。看不出是朝陽還是夕陽的金光,斜斜地照在兩人身上。
這樣的小說,簡直是個童話故事。但是,小龍卻有能耐把人物的心理寫得絲絲入扣,令讀者完全信服他們的行為。這對作者來說,需要等同於小說中那個男生的自信和決心。小龍的小說幾乎都有這樣的特色,那就是把不可能的處境寫成可能。她的小說沒有幻想或超現實的成分,全都是切切實實的生活描寫,但卻一致建基於某個不合人之常情和常理的設想。
兩年後出版的《風流》也是如此。一對三十多歲的男女,三年前各自單獨旅行時,在普吉島的一間度假酒店認識。樣子風流的男人,主動接近女人。女人起先反應冷淡,但漸漸又覺得男人有趣。當夜兩人半推半就,發生了關係。第二天開始把臂同遊,猶如親密伴侶。旅程結束,大家都獲得了意想不到的驚喜,但卻沒有更多的期待。男人在回港的航機上還戲稱,下次有機會再結伴旅行。之後,他們回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就像只是做了個愜意的綺夢。幾個月後,女人完成了一件十分勞累的工作,想找個地方散散心。她想起了男人,聯絡上他。他立即請了假,陪女人去了沖繩。自此,兩人就成為了「旅伴」,每隔幾個月一起旅行,其他時間卻各自生活,從不見面。他們沒有詳細查問對方的背景,也沒有去確認真假。他們互相分享的,就只有每年那總共二十多天的共處。兩人以這種關係度過了三年,而小說集中敘述的,是三年內最後的一次旅行。這次的地點是馬爾地夫。在度假酒店裡,他們遇到一對度蜜月的年輕新婚夫婦。對方誤會他們也是一對夫妻,而不知何故兩人也沒有否認。由這誤解開始,他們發現彼此的關係悄悄地出現了變化。兩人不再像之前的瀟灑,開始多了顧慮、不安、猜疑和試探。他們都想確認對方究竟是玩票還是認真的,但在確認之前又不能暴露自己的意圖。雙方都以假求真,結果卻又假戲真做。這對「最佳旅伴」究竟能不能成為「最佳伴侶」呢?小說下半部有許多幽默而又諷刺的描述。結果貌似風流的男人宣稱,他由始至終都愛著女人,而且一直在默默地等待適當的時機向她表白。女人卻說她其實已經結婚,並且有一個六歲的兒子。最終她拒絕了男人,決定以後也不再跟他見面。遊戲規則已經被破壞,大家失去了維持關係的基礎。至於兩人所說的是否屬實,則無從稽考,似乎也無關重要了。
如果《朝暮》表達的是對超越肉體的愛情的信任,《風流》則彷彿做出一個反論,說明愛情是無法把握的虛幻事物,只有肉體才是實在的東西。有些讀者對這樣飄忽的觀點感到無所適從。《風流》似乎是小龍的小說中評價最差的一部。有人覺得此書言之無物,只是靠一對偷情男女的傷風敗德做賣點,結局的不確定也只是故弄玄虛。甚至有人認為,龍鈺文已經江郎才盡,原本便已經十分狹隘的識見再變不出什麼新花樣。至於採取文化批判角度的論者則斷言,龍鈺文由始至終也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品味的二流小說家,既無意探討女性受壓迫的處境,也無力給弱勢者賦權,極其量也只是賣弄一下花巧的構思,寫些討人歡喜的奇情故事。
小龍心裡並不是不在意批評的。她還未超脫到那樣的地步,但她也不是個輕易認輸的人。大概在《風流》出版前後,內地興起了一股港台文學風潮。小龍的前期作品,也乘著這潮流出版了簡體字版本。不少港台作者都紛紛回到內地活動,尋找更大的市場和新的發展機遇。小龍也曾在出版社的安排下,參加過內地的書展,但對國內文化人的交往方式感到不慣,也對疲勞轟炸式的媒體採訪感到厭倦,很快就謝絕了同類活動的邀請。她發現,自己對於專業作家的理解已經發生變化。她堅持的與其說是工作流程和回報上的專業,不如說是創作態度上的專業。秉持著這樣的態度,管他是挫折還是機遇全都拋諸腦後,她在2012年寫出了新作《無端》。
《無端》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好像沒有什麼特別。要說故事的話,就是一個老掉了牙的紅杏出牆的故事。要說新意,就可能是那紅杏根本就沒出牆的理由和意圖。所有事情也是「無端」發生的,至少是表面上如此。故事的主人翁是一對小夫妻,兩人在中學時代是同學,畢業後沒有考進大學,一起在職業訓練學校進修餐飲業課程。女生從小就喜歡弄糕餅和甜點。中三的時候,她把家政課上烘的一個麵包送給男生。那是一個什麼花巧也沒有的,外表香脆而內裡鬆軟的十字包。兩小無猜的感情,就是這樣開始了。男生為了陪伴女友,也決定學習西式麵包和蛋糕製作。兩人學成後在酒店西餐部打過幾年工,女生甚至獲派到法國短期深造。後來男方向家人借了筆錢,和女友一起創業,開了一間小餅店。青梅竹馬的兩人也順理成章結了婚,夫妻倆一起為事業而奮鬥。餅店的口碑甚佳,生意不錯,但經營成本亦高,實際所賺不多。妻子後來利用臉書做宣傳,又上載自己的甜點製作短片,加上本人樣子亦甚甜美,在網絡上瘋傳起來,得了個「美女廚神」的稱號。店子的生意好起來,妻子連續不斷地接受媒體採訪,甚至獲邀開設專屬的節目,廚具和食材品牌亦爭相送上贊助。妻子變成了公眾人物,忙得不可開交,收入亦水漲船高。丈夫對妻子打出名堂十分高興,但內向的他情願全力打點店子,鎮守後方。後來一位當初幫妻子拍攝節目的監製,主動提出成為她的經理人。兩人開始打造各項發展大計,關係愈來愈親密。相反,丈夫只懂老老實實地躲在廚房,每天親自焗製麵包和西餅。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夫妻的感情出現了變化。妻子經常因為工作而不回家,而丈夫就只能默默地等待。成為紅人的妻子,遵照經理人的意思,開始注重打扮,刻意經營自己的形象。她抱怨丈夫沒有遠大的眼光,不肯與時並進,永遠像個長不大的少年。丈夫的靜默和忍讓,在妻子的眼裡卻變成漠不關心。在一次到外地拍攝美食節目的時候,妻子跟經理人發生了關係。之後兩人維持著半公開半祕密的交往,連丈夫也察覺到事情的跡象,但他什麼也沒有說。大約半年後,妻子發現自己懷了經理人的孩子。她和經理人商量過後,決定跟丈夫離婚,而經理人亦答應跟她組織新的家庭。丈夫沒有提出反對,只是在簽署離婚協議書的時候忍不住流了淚。他交給妻子一個他親手做的十字包,說:想不到我們由吃麵包開始,也由吃麵包終結。妻子一邊吃著麵包,一邊流著眼淚。她忽然感到奇怪,兩人到了最後,明明依然還深愛對方,但是,為什麼卻會走到這個地步?可是,她已經不能回頭。兩年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女子回到餅店去,想看看變成了什麼模樣。那間小餅店還在,但已經易手,連名字也改了。她進去問了問店員,從前的老闆去了哪裡。新的老闆走出來,告訴她,那人半年前已經急病去世了。
只聽情節,這是個不折不扣的通俗愛情故事,感覺甚至有點過時。然而,小龍集中所有力量,一直緊扣著「無端」這一點,通過無數看似沒有特別意義的生活細節,不動聲色地把一對恩愛夫妻的關係推向無法挽回的結局。第三者的出現,也只是所有「無端」中之一環,並非獨立的決定性因素。而事情亦不能簡單地歸咎於任何人的道德缺失。愈看愈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是人心的難測和人事的無解。一切變化,都是數不盡的因緣的互動和累積。到當事人發現事情發展的勢態,要推倒重來已經太遲了。「無端」這一本質,實在是生命裡最可怕的東西。它能生成一切,也能毀滅一切。就連最深厚的愛,也無法抵擋「無端」的侵蝕。
也就是這樣的實力,令《無端》得到本地的一個長篇小說大獎。其中一位評審說:「對於小說傳統題材和敘事方法的回歸,在當今標奇立異和形式主義的文學界,是個難得的現象。」這樣的意見真可謂完全捉錯用神。不過,這個關係不大。那三十萬元的獎金,終於有點諷刺地實現了小龍追求多年而不得的經濟獨立和專業作家級的報酬。至少是短期內如此吧。她決定運用這筆歷來最大的收入,到英國去旅居一年,進行新的創作計畫。這是個完全獨立的決定。我做為丈夫,只須做出精神上的支持。其實,自《無端》完成之後,小龍的寫作停滯不前,已經差不多三年了。這筆獎金無疑是一陣及時雨,讓她可以完全自由行動,尋找創作的新動力。 圖:唐壽南。
圖:唐壽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