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即將進入之新聞內容 需滿18歲 方可瀏覽。
徐禎苓/黑頭來了(審查就像一把大篩子)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
〔徐禎苓/自由副刊〕
透早起來,屋外的大人們正低聲說話,那小心翼翼的模樣,似乎暗渡著一個不能公開的祕密。
阿慶幾乎沒看過這種情況,大人們刻意把聲音壓得極低,邊說邊鬼祟地張望。到底發生什麼事?他躡手躡腳溜到門邊,拉長耳朵,聚精會神地偷聽。
尖峰巷巷尾的電線桿上,竟然出現一行粉筆字,上面斗大寫著:「推翻蔣政府」。
這非同小可!在戒嚴的年代。
到底是誰寫的?大家都在討論。
阿慶還想多聽些線索,就被母親催促上學了。鎮日,他反覆琢磨那個祕密。誰那麼大膽?為什麼要寫這種話?如此想,就迫不及待渴望放學回家。
下午,他走回尖峰巷,已匯聚大批憲兵。家家戶戶緊閉大門,平常在溪邊聊天的婆婆媽媽們,今天也提早收工。誰都怕受牽連。萬一黑頭車來,怎麼辦?
當時,只要巷口出現黑頭車,大家都會迅速躲回家,而且大門深鎖。這早已是不成文的默契。大家繪聲繪影地謠傳:警備總部的人會直接闖入家裡,然後拿著單子一個一個問人:「你是不是╳╳╳?」若是,不等你辯解,當場抓人上車。只要搭上車,就永遠不可能回來。
聽說有位中學老師就搭上了黑頭車,一個月過去,兩個月過去,始終沒有回來,也沒人知曉去了哪裡,或者,還活著嗎?他的太太心急如焚,四處奔波請朋友幫忙,然而,有些朋友為了自保,趕緊切斷關係;有些朋友用盡人脈也徒勞歸返,先生的消息一直苦無著落。這段時間,她想像先生可能在監獄裡遭受的折磨,就會忍不住嚎哭。隨著時間拉長,哭泣裡疊加怨與恨,她感覺所有的負面情緒正在吞噬自己。
即使人在監獄外,也活得像煉獄。她被熬磨到只剩下最後一個意念──找到先生。她做足最壞打算,但哪怕處死了,警總也得給出交代。身為家屬,她必須承擔,也必須長大,否則人很容易就被恐懼挾持了。忽然,她剛強起來,決定到台北法院申訴。
一個女人,從新竹徒步了七天才抵達台北。那時候,一個女人,一個只會說日語和閩南語的女人,在威權面前不只微不足道,還頗令人厭,裡面的官僚沒有搭理,連哄帶騙把她趕了出去。她始終不知道先生是死是生,即便日後解嚴了,先生下落依然不明。
傳說一則又一則,每多聽一則,就讓警總的形象在心底顯影一次。黑頭車不知不覺牽動起人們的恐懼,勾連死亡。
大人的恐懼是會蔓延給小孩的。只要哪個小孩無理取鬧,情緒失控,大人總會怒斥:「再哭!等下黑頭來把你抓走!」小孩慢慢深諳黑頭車的意思,立刻安靜下來。警總已經住進人們心底,不分年齡。
就像昆仔晚上聽廣播,頻道轉啊轉,竟莫名調到對岸的廣播電台。那脆口的京片子、鏗鏘的語氣,連電台的人到底說什麼都不清楚,身旁阿鳳、阿美、阿慶一家子著急地喊:「快點快點!」快點轉台。因為連小學生都知道,電線桿上有條軍用線,會全方面竊聽各戶人家聽的廣播內容,若涉及匪諜、禁歌,一概抓上黑頭車。
當阿慶終於經過那支寫了粉筆字的電線桿,忍不住多看一眼。可惜,被憲兵蓋上白布,像電視上演逝去的人臉上覆著白布,什麼都看不到,連記憶的機會也沒有。
白茫茫。
回到家,阿慶問阿美關於電線桿的事,她立刻扭過頭,答了聲不知道,自動屏蔽敏感問題。語畢,又想了想,再回過頭說:「生活就是難題了,你在乎那幾個字做什麼!」
母親聽到阿慶的疑惑也大驚失色,連聲喝斥:「小孩不要亂講話!等下黑頭來了!」接著把頭探出外面,看有沒有人偷聽到什麼。阿慶嚇到了,只得硬生生壓下正在發芽的好奇心。
他長大以後,才慢慢曉得這就是白色恐怖。每個人都在自我審查,審查就像一把大篩子,篩去正義勇敢,或各種反思能力……到後來,就像尼采說的:「人的生存令人感到莫名的恐懼。」
那件事情之後,尖峰巷的人很快回到軌道,每天上工上學,比起知識分子口中的意志,這群白丁更在乎生存。現在,粉筆字到底是誰寫的,已經不重要了。這世界上總還有比粉筆字更迫切的事情。
譬如,黑頭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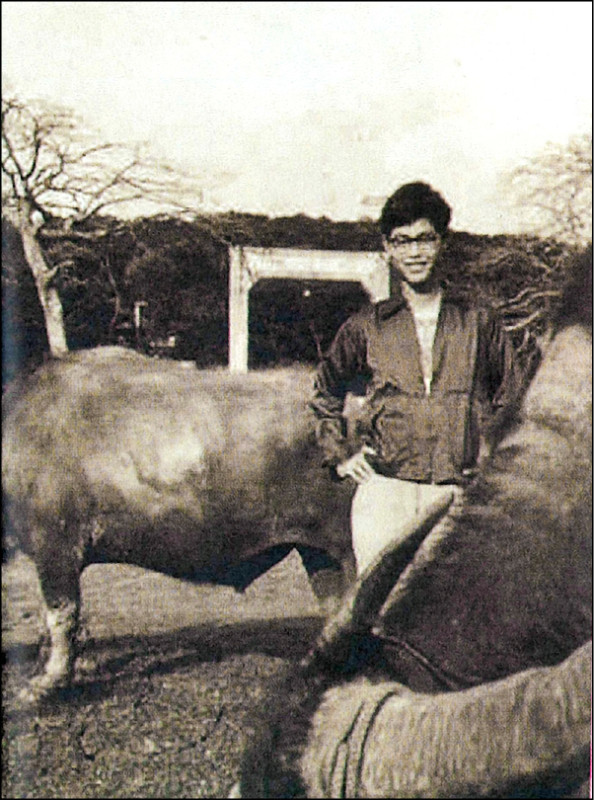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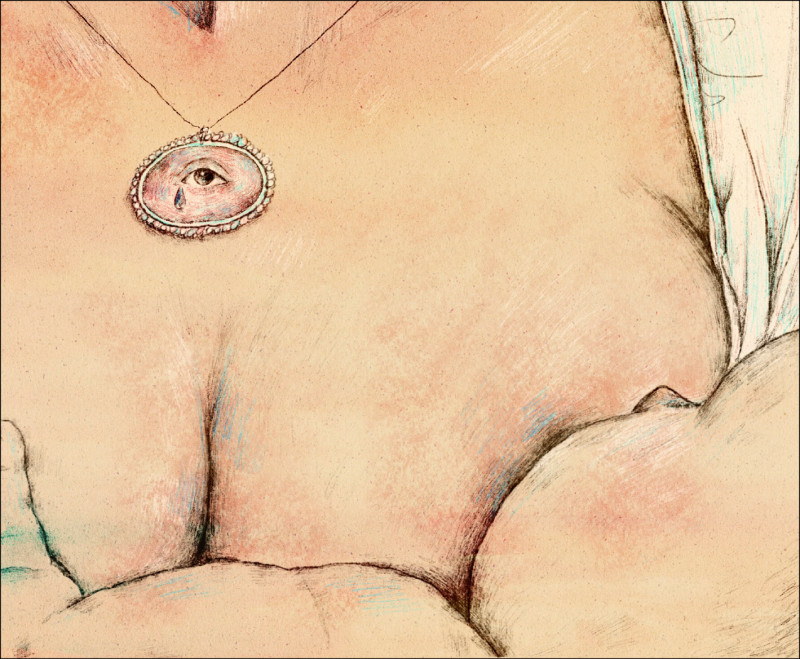

網友回應